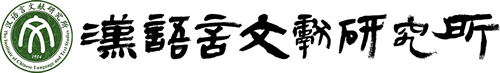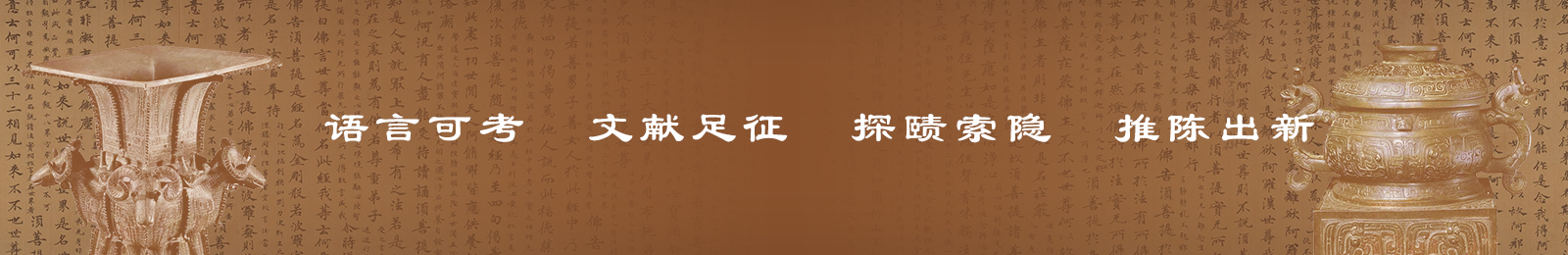我所教师出席世界汉字学会第十一届年会
2025年10月16日至2025年10月20日,世界汉字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日本大阪教育大学(天王寺校区)成功召开。本届年会以“面向未来教育,为AI赋能世界汉字学知识体系”为主题,由世界汉字学会、(日本)国立大学法人 大阪教育大学、(韩国)庆星大学韩国汉字研究所、(中国)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联合主办,来自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匈牙利等国及中国台湾、香港地区的百余位学者、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,共同挖掘汉字学研究的新方向,助力跨文化学术交流与教育创新事业发展。

我所孟蓬生教授、黄程伟讲师,以及文学院何山教授赴会交流,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汉字学的创新发展路径。

孟蓬生教授宣读论文《“西”“巢”同源说——兼论上古汉语的宵脂通转现象》,认为甲骨文“西”字有两种写法,其中一种写法与甲骨文“巢”字上部相同,故“西”字本象“巢”形已经成为学界共识。上古音宵部和脂部可以发生通转关系,因此从字形的角度看,“西(脂部)”和“巢(宵部)”可以看作同源字;从语词的角度看,“西”和“巢”可以看作同源词。古音宵部和幽部相近,因此宵脂通转跟幽脂通转都可以看作甲类韵部(或称收喉韵部)跟乙类韵部(或称收舌韵部)的通转现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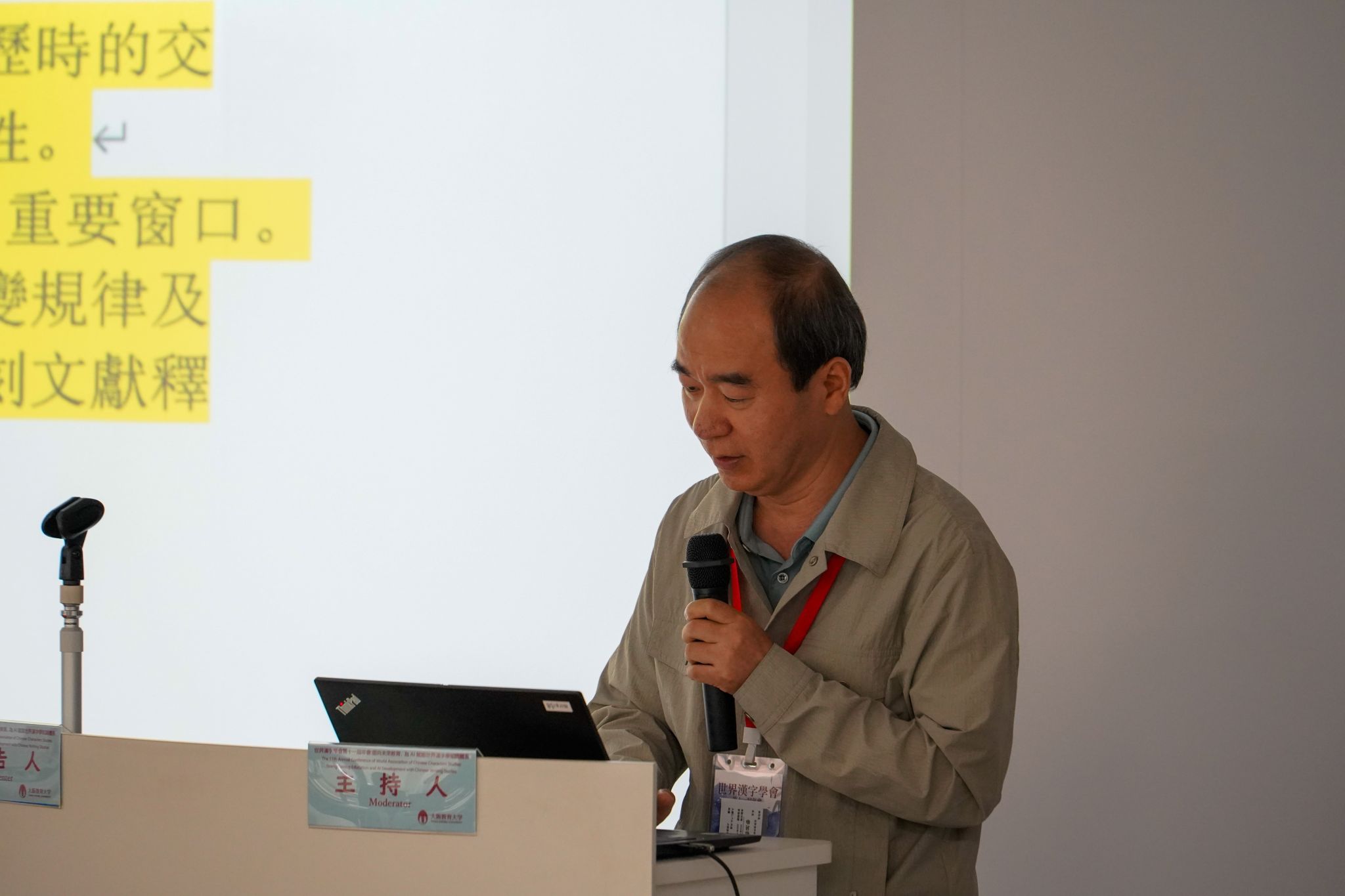
何山教授宣读论文《宋辽金元碑刻隶古定字研究》,认为宋辽金元碑刻古文字遗留因素非常丰富,其隶古定字形来源多途,形式多样,既有传承甲、金、战国文字、小篆、《说文》古文等古文字形的隶定字形,也有与传抄古文隶定形相合的字形。《说文》小篆等篆文隶古定字形占比最大,其次为传抄古文隶古定字形。整字隶定形和构件隶定形皆有使用,又以后者居多。宋辽金元碑刻隶古定字于传承中有发展,于保守中有创新。考察碑刻隶古定字形源关系、演变规律及时代特点,具有汉字本体研究的重要意义、汉字学科建设的理论价值和碑刻文献释读整理等实践参考作用。

黄程伟讲师宣读论文《读东汉〈赵宽碑〉札记一则》。东汉光和三年《赵宽碑》有一“□”字,其文例为“叔子讳璜,字文博,缵修乃祖,多才多艺,能恢家~业,兴危继絶,仁信明敏,壮勇果毅,匡陪州郡,流化二城,今长陵令”。文章综合字形、文例以及前人观点,认为该字当视为“袥”之换声异体字。至少在东汉时期,表示“开拓”“扩展”义,“斥”“袥”“拓”三字并用,而且“袥”字存在一种异体写法作“□(𧙝)”形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载“夫道者,覆天载地,廓四方,柝八极。高不可际,深不可测,包裹天地,禀授无形”,高诱注“廓,张也。柝,开也。八极,八方之极也,言其远。柝,读重门击柝之柝”。然而《淮南子》许慎注与高诱注不同,作“㡿,拓也”。前人对此聚讼纷纷。文章根据前述汉碑反映出的文字使用情况,认为东汉时期《淮南子》当存在多种版本,高注本作“□(𧙝)八极”,许注本作“斥八极”,两者并行不悖。